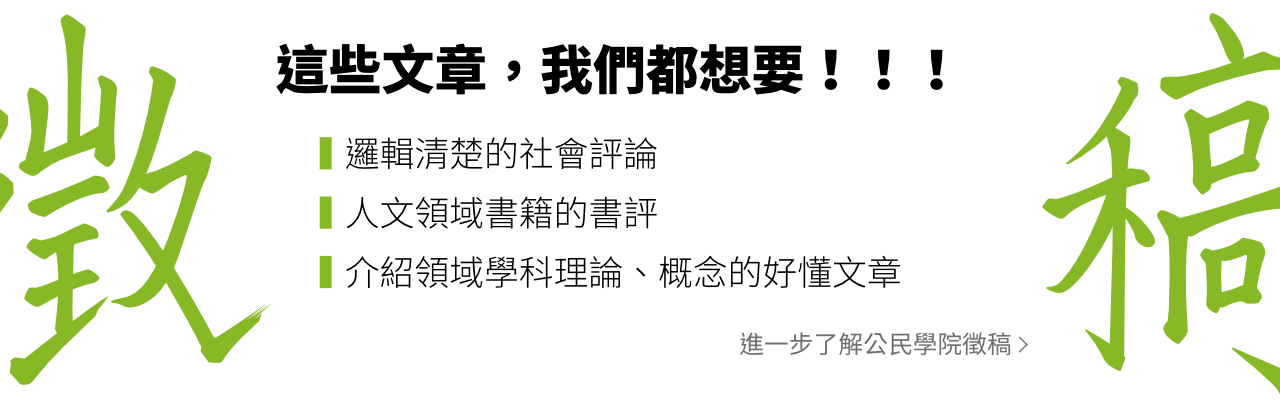圖/陳小冠
圖/陳小冠對社會學的無知,正反映台灣社會對不公義的無感
2014年春、台灣社會經歷一段學運與社運的市民社會發展期。在這過程中出現一些有趣的文化現象是值得探討的。部分的左派知識份子概括承受了「暴民」的唆使者或煽動者的指控(本文所指的左派知識份子,乃法式「intellectuel」之定義,特指實際參與社會事物的學者,並擁有捍衛公義與平等等左派思維之立場)。而其中「社會學」則被點名成唯恐天下不亂的禍源學問。社會系所的相關學生被質疑進入社會之後可能成為秩序的破壞者或搗亂者、家長們開始憂心自己子弟學習這種批判精神後將在社會被貼標籤、以及在腦中將被改造成偏激份子或憤世嫉俗。甚至社會系也被點名,被詢問他們是在「衝啥」?隨即(直到目前),左派知識份子們還忙於招架這些質疑、攻擊、、、。

然而、上述這個文化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在我們檢視這個文化現象前,容我們問一個問題:台灣社會對社會學以及相關啟蒙批判學科的無知、無視、以及「妖魔化」是不是一種將它塑造成「代罪羔羊」的策略呢?這樣把「社會學=教唆動亂」做了連結之後,反映出來的是不是一種中產階級式的期待與想像呢?一種「本來無爭端、何處惹暴動?」的類結構功能論的思維呢?
在此,不只拉出美式「結構功能論‧價值衝突論」的辯論;同時更重要的,應是台灣社會對於秩序、衝突、正義公義的堅持等概念是作怎樣的慣性思考?在後冷戰時代[i]的今日台灣,長期沈默的左派思維與馬派關懷,能否深入人心,成為至少可被欣賞的質素甚至進一步成為核心價值之一?而對社會學的無知、以及進而調侃、奚落的態度,背後彰顯怎樣的集體潛意識思維?且讓我們學Freud來對這些「反動者」作個精神分析吧!
「社會失序」是常態,不是牛鬼蛇神
中產階級的思考,冀求一個安和樂利的平穩社會。不過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不會所有的情境都在秩序之中。社會學家涂爾幹甚至認為,維持在可被接受的自殺率之下的社會,並不能算是「病態」。自然、涂氏不是認為自殺是「好事」,而是他深諳社會結構的屬性以及社會運作的邏輯,並瞭解波動在社會的進程中是一種「常態」。
從革命的角度來看,暴動與推翻暴政乃是必要之惡(沒有當年的法國大革命、人類的民主紀元將要延後;沒有野百合的「暴民」,萬年老國代將繼續馳騁於國會中);從成功鎮壓了起義之士的君王而言,他則在處理一件「平亂」(歷史換人寫、英雄變狗熊!)。所以這次社運與學運中的參與者,究竟是「義士」還是「暴民」?我想社會學家與執法人員會有很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社會學者不見得站在權威當局的一方看事情,而更傾向從社會公義的角度、以及弱勢發聲的角度來體檢整個社會事件。不過,這並不代表社會學是一門專門教唆造反的學問,只是它不排除這種非常之手段。

也正因為如此,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一次與郊區群眾運動的公民座談完指出:「我不是說你不能去火燒車,但是你必須知道為何要去燒它!」這位「暴民社會學家」在2002年去世時,法國三大報以頭版來紀念他,而解放報(Libération)則以頭版全版面來悼念他。左派老國對社會學以及社會學家的尊敬、台灣社會是否可以參考呢?
是否到了該揚棄「藍綠框架」的時候了?
此次社運的另種反動聲音,則援引台灣過去廿餘年來所習慣的藍綠分析架構,指陳此次的群眾運動即為某營政治人物延續其政治影響力、累積政治籌碼的重要一役。並搜尋哪位學運領袖實乃哪些特定政客的子弟兵等云云,意在作政治鬥爭或者癱瘓執政當局之運作。此刻,藍綠迷思儼然成為台灣島上分析政治現象、連帶地、分析種種重大社會現象或議題的「百寶箱」,只消把發生的社會事件放入這個「藍綠座標」的照妖鏡中,妖魔自動即能現身而無所遁形。多麼好用的「萬用分析座標」!
這個在台灣從六0年代原本被陳述為「省籍問題」、經八0年代的「族群問題」到九0年代的「統獨問題」,以至今日修成正果的「藍綠分化」,究竟為台灣的前途、社會剖析帶來的是口水之戰,還是洞悉的見解呢?有慧眼的市民可以自行分辨與檢測,不用本篇文章另作評論。不過社會學並不是天真地認為政治力完全沒有插手於社會運動之中、並甚至影響整個抗爭的運作方向甚至結果。由政治主題所繫的鈴、最後還需政治力量來解之,這是必然。
然而本文在此另外想強調的觀點,卻是從社會力的角度出發,指出此次社會運動與二十數年前(含野百合)的抗爭相比,整個市民社會的厚度是不同的:民眾的動員方式、社運人士的組織運作方式、以及自主的程度,並不見得是權威當局或者反動人士所想像的這般簡化:被教唆、暴民、藍綠互鬥等等。這時、該檢討的似乎是這張照妖鏡,是否也該升級了,甚至揚棄(Aufhebung)了吧?
世代間思維的差異反映出怎樣的「務實」世風?
學運的反動力量也來自學生家長。當然不是所有的學生家長都反對學生走進立院、或關心國事(不管他們以何種程度或方式關心),不過基於關心子弟的安危,不少家長還是選擇站在監護的角色。學生與家長之間想法的齟齬,是否也顯示了這些家長與其子弟在面對「參與國事」的想法與做法上有所差異?
這些擔憂讀社會系的孩子出社會後將被貼標籤的家長,其實早在當年其子弟選填科系志願時,即已呈現出其對社會學的不瞭解。從父母的角度出發,教養出一個有競爭力的子弟,必須要讓他們進一個有專業訓練、可以考證照的科系就讀。從此脈絡、社會學是沒有市場的,所以不用去研究與瞭解、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每年系所招生以及夏日的校園導覽中,學生家長最常問的問題是:「讀社會學出去能做什麼呢?」而在證照掛帥、大學正在技職化以及經典人文教育被無視化的時代氛圍中,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因為答案要配合這個功利(一說「務實」)角度、就業能力的提問框架來對焦,先天上已經與這門學科的原始屬性有太大的出入;當然、也與大學作為「學問」的教授之處的初衷全然分離。
所以回答,要以跳脫連帶點醒的方式進行:「學社會學出去不能做什麼?」在社會系學到的能力、是一種陪你走完整段人生路的思維能力、是一種深化人文學識底蘊的培養、是讓我們反思民胞物與、社會公義以及一種養成社會瞭望台上守望者的關懷。在專業分工的時代、它不是一種純技巧的培養,卻也不會阻擋人去進而學習其他的專長技巧。或者、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社會學這個科系太也奢侈,誠如閩南諺語所言:「生吃都不夠、還能曬干?」不過、當一個社會缺乏這樣的理想、良心、公義原則、正義需求,以及人文思維時,被我們訓練出來的下一代、是否只會淪為「訓練有素的狗呢?」而整個大環境是以技職教育、務實功利作為培養子弟的主流思維氛圍,又怎麼能挺年少的大學生這種捍衛正義的「脫序行為」呢?這樣,與安定力量對抗的,還只是社會學、以及社會學之流所教唆出來的學生與「暴民」嗎?
在這次「社會動盪」的過程中,如果該反省的,不應該是社會學及其所貢獻出來的價值,那麼,我們該檢討的,是否應該是那種鄉愿的、只求安定不願承受動盪代價的、希望孩子回到主流思考下的主業學習,這一種息事寧人的集體潛意識?
對社會學的無知,反映了左派關懷的孱弱
後冷戰時代的台灣社會有深刻的左派關懷嗎?我們這個社會,是否具備了為弱勢發聲的穩固基礎了嗎?社會資源的分佈平均、合理了嗎?如果今次服貿議題撇開藍綠框架、亦暫不提「民主/獨裁」對立及台人潛意識中的「恐中/反中」情結;那麼,在全球化淫威下不得不加入各式經貿協定的台灣,到底如何在全世界的經濟版圖中找到利基?跳回較小格局則是,此次服貿的各式設定中,又是否應將分析單位還原到各行各業的總體評估上頭,先來進行一次總體檢呢?評判其後座力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在九0年代之後,號稱進入福利國時代的台灣,難道到頭來要落了個「左皮右骨」的窘態嗎?

社會學在「衝啥」?它,就是剛剛好可以在這個無人能逃脫得出之全球化浪潮下,於台灣甫進行完的「服貿/社運」政經攪動之中略盡棉力。從最宏觀的全球層級也好、從境內的資源分配也好、從集體潛意識的理路分析也好(剖析藍綠迷思、憂心技職教育掛帥將失去的人文性)、從市民社會的厚度慢慢成形的觀察也好,試圖對當前台灣的政經困境進行一種盡可能全方位的把脈,並研擬可行之應對之策。或至少嘗試向當局提出警語與建議。社會學在此、既是社會的把脈醫師、復為瞭望台上的守望者、但同時也是一位準國師的學問。
社會系在「衝啥」?在於嘗試培養出既有專業的、深度的分析能力、又具有厚實的人文人性的社會關懷、並對公義堅持的公民。這門至今對台灣人民仍極為陌生的學問(甚至是懷有敵意的學科),不正亦反映出當前我們對於社會不公義習慣性地息事寧人(嚴重者甚至漸趨冷感化)、以及左派關懷的孱弱嗎?
NOTE
- 台灣於戰後處於冷戰與內戰雙重結構下,而造成馬派思維的闕如,已由文學家陳映真與清大教授陳光興提出,可參見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