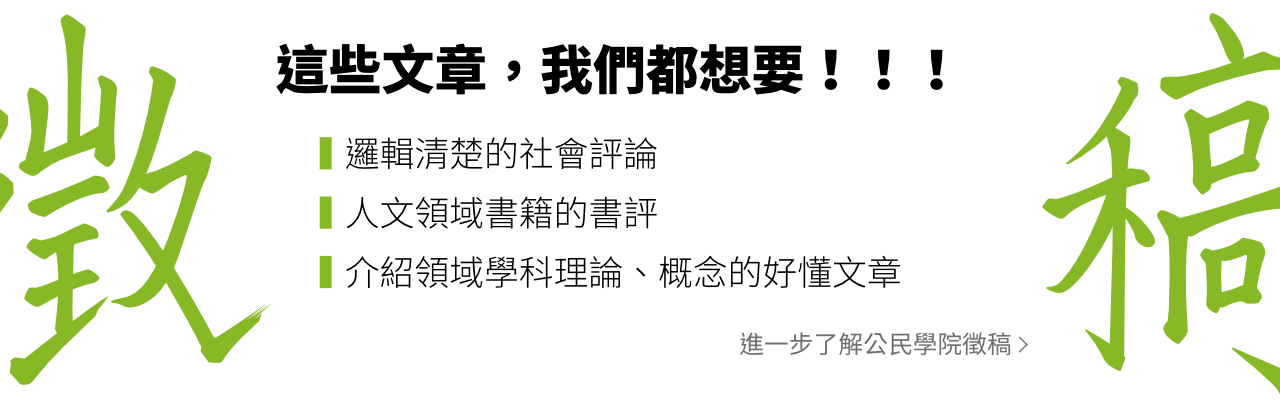圖/陳小冠
圖/陳小冠恐懼的修辭:恐怖主義與民主的反挫
恐怖主義造成的最大創傷:恐懼的形成
這不知已經是在911事件後,我的第幾次通過洛杉磯機場(LAX)海關了!日前赴美參加一場學術研討會,通關又花了一個多小時,當時網路不通,完全無法打卡或上網,在號稱全球連結的時代,那等候的一個多小時,像是與當代世界隔絕。911事件十多年後,宣稱要「改變」(Change)的美國總統繼續連任後,LAX移民檢查關卡還是一樣擁擠、一樣緩慢、一樣的不耐與不滿。

漫漫無盡的等待、移民官冷漠、冗長、嚴厲的質詢、類似刑犯的攝影與指紋按壓程序,這些場景的鋪陳,不正是在提醒這些即將入境的美國公民與國際人士,恐怖主義存在的真實嗎?不過,這樣的場景,卻正是恐怖主義對民主體制最成功的恐嚇與重創。
事實上,恐怖主義真正令人恐懼的地方,不僅僅只是在恐怖行動當下對於受難者所造成的重創,更恐怖的是,造成社會擴大管制民主體制、自由社會中的權利,以及對自我生命尊嚴之自我管制。
我們的恐懼情緒指數,預測了我們自由尊嚴喪失了多少
在防止恐怖主義的巨大壓力下,我們或主動、或被動地犧牲了民主的言論、自由的行動,並且在官僚的「協助」與擴權下,我們身為一個自由人的尊嚴消失在監視器與指紋機下。甚至,在「預防、嚇阻」恐怖主義下,官僚們玩弄權力,擴大了他們的種族與階級歧視。因此,在這樣嚴厲的反恐行動與機場安檢工作中,我們應當提問:是誰會被滯留?是誰會被搜索行李?那不就是有色人種、勞動階級、非基督徒嗎?

在面對全球於911之後所產生的恐懼氛圍,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奈及利亞)Wole Soyinka指出,恐懼氛圍與恐懼的建構,其背後正是權力用來支配我們在日常生活的行動。計算我們的恐懼情緒多少,就可以計算出我們喪失多少自由與尊嚴。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或許一直到高鐵炸彈事件,才可能通過媒體的渲染,感受到些許恐懼的氛圍。但是,對於成長於戒嚴時代的中年以上台灣人民,這種由統治者權力運作所創造出來的「恐懼氛圍」,一點都不會陌生。在那個「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戒嚴、白色恐怖年代,統治者利用媒體控制等方式,將「共產主義」與共產中國妖魔化,進而形塑恐懼的氣氛,箝制人民各種行動、言論自由,讓多數人成為「沉默的串謀者」,而使號稱的民主與自由體制,成為是威權政體的裝飾品。
誰在熬煮恐懼修辭湯? 政客跟我們!
不過,在這樣肅殺的恐懼氛圍中,全球反恐行動成功了嗎?至少在美利堅合眾國,這個號稱世界警察的「民主」國家,我們看到恐怖主義所散佈的恐懼並未在911的10年後消失,恐怖攻擊也並未因為「嚴厲」的機場安檢,而預防了上週4/15日發生在波士頓馬拉松的悲劇。在持續不斷的全球恐怖攻擊行動中,我們見證到了民主體系的脆弱:脆弱根源並不在民主理念自身的錯誤,而是政客與官僚,如何利用恐怖主義的威脅,或者其他各種形式的恐懼,恐嚇人民,創造了他們自身存在與擴張的理由、限制了人民行動的自由、擴大且合理化原本存在的社會歧視。如Soyinka所說 :
恐懼的散播者,要不就是讓世人凝聚,要不就是設法使世人盲目。他們利用獨白般的修辭來鞏固權力,引發歇斯底里,製造敵我對立,使人拋棄理性與個體。這種魔咒的美妙之處在於他們永遠都有辦法把複雜的事件和全球關係濃縮成一碗修辭湯,這碗湯雖然有礙消化,但保證你喝完之後心滿意足。

進一步的社會學觀察則告訴我們,統治者這碗難喝的湯,並非單靠他們與官僚的權力壓迫,就可以讓人民接受。Charles Tilly,當代重要的歷史社會學者,在面對自身與癌症病魔的搏鬥,以及911之後的社會,他開始討論,人們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變遷,是如何透過給定「理由」(reason)的方式,來定義彼此之間社會的關係,並重塑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他觀察到,當日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時,人們特別期待簡單快速理由的給予。為何會遲到?為何生病了?這麼可怕的災難(恐怖活動)怎麼發生了?當人們的常規生活秩序被打擾了,我們便會希望可以以最快速的方式,將這個不確定、意外的事務,給予規範,並且將之安置在一個新的、明確的社會關係與秩序之中。
Tilly認為人們依據我們與他者(理由給予者reason giver與接收者receiver)之間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給定理由的方式。透過這些理由的給定,我們穩固了原本產生衝突的社會關係。理由給定模式有四個不同的層次:社會慣例(conventions),亦即一般社會普遍接受的陳詞,例如:路上塞車了、生病了所以作業遲交等。其次是簡易的故事(stories),這其中有簡單因果關係的敘述。第三個層次是行為準則(codes),這層次理由的提出,關切著所要採行的行動,因此具有法律或宗教上的意涵,例如:獎勵的提出、法律的判決等。最後一種,則是技術報告(technical accounts),是相對複雜的說明,通常對於非專業者是難以理解或費時去認知到。
日常生活常規遭破壞後怎麼辦?Charles Tilly的「理由給定」
通常,我們會以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來給定不同層次的理由,藉以來建構、重塑彼此的關係。換言之,透過理由的給予與接受,我們「安置」(placing)他人,也被他人「安置」(be placed)在社會之中。
在一般的社會情境,我們會快速的通過社會慣例,給予理由來簡單地確認、修補或否定當下正在進行的社會情境。亦即,通過社會慣例式地理由給予,我們快速的依據彼此的社會關係,解決一個看似衝突的場景(在車站撞到陌生人了,儘快說聲對不起,然後離開)。
但是在面對重大事件或不熟悉的場景發生時,例如:遭遇重大的挫敗、關鍵的勝利、從未聽聞地夜半怪聲等,我們都不會只滿足於一般性的解釋。因此,我們會透過一個有因果關係的故事(公司給我大筆的獎金,因為我勤奮的工作與優異的表現,特別是我賣掉了幾百台電腦…),來正當化自己的狀態。
至於法律或宗教的理由,則很清楚的跟理由給予者,其下一步可能採行的行動相關。一個公司的律師對一位剛提出一份企業計畫的工程師說:「這樣的企劃會違背法令!」通常,聽到這樣的理由,就表示討論結束了,而且「理由充分」。對於使用規範、準則(codes)作為理由,雖然時常產生許多荒謬的場景,但是,對於那些執行者來說,卻是保護他們自己最好的方式。這普遍可以在台灣當前的政府組織,上自總統、下至各級政府公務員都可以時常看到,在面對許多爭議議題時,他們通常就是以一句:「依法行政」,就堵塞住所有對問題解決的可能性與進一步的討論。最後,技術報告則讓事件的參與者們,可以有一個更詳細的因果關係,去理解事件發生的理由,並且嘗試去提供更專業的解決問題方案。

當然,在突發事件時,理由的給予就會滿足並降低人們對於變動社會情境與不穩定的社會關係時所產生的不安。但是,不論哪一種理由的給定,一定都難免面對各種質疑與挑戰。如果一個理由的給予過程,沒有遇到任何挑戰,那通常都跟理由給予者握有一特定權力位置有直接相關。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高級官員與專家學者通常就會扮演這樣的角色,在面對諸如恐怖行動、核電廠等議題,他們就會以自身的權力與權威,透過不同的理由組合,給予事件的說明,然後確認新的社會關係與情境。而在一般事件的時候,人們則通過不同的理由給定,透過某種協商、質疑的歷程,來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確認兩者之間角色的平等或不平等。
日常生活的「沈默串謀」讓統治者得以遂行其權力意志
也因此當面對諸如911等的重大恐怖行動時,人們會嘗試先用簡單的方式給予理由,來協助自己與他人理解事件的可能原因,進而找尋出自我對應的社會生存模式。但也正因為人們傾向於選擇簡易的方式來重構崩潰的秩序,這就讓統治者與權力者,得以藉由大眾選擇「沉默」、「否認」事實,以逃避痛苦、降低自身的恐懼與尷尬(為何我當時沒有做… ,要不然,他/她就可以 …)的集體機制,也就是沉默的串謀,來遂行他們的權力意志。以色列出身的學者Eviatar Zerubavel分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沉默串謀」這股集體力量形成的因素之一,就是因為出於「保持團結」,亦即Charles Tilly所認知的「社會秩序與關係的重建與鞏固」,而阻礙了誠實與開放性溝通的可能性。(1)

我們觀察911之後,恐怖行動並未因恐怖首腦的逮捕而消失,全球不同族裔的人民,也並未因為這些反恐行動的嚴密監控,而生活的更安全、更和諧。相對的,恐怖主義的真正根源:全球性的資源分配不均、區域資源的掠奪、社會的階級不公與歧視、偏見等,卻從未認真的公開討論與解決,因為人們選擇放棄挑戰主流社會所存在的議題,寧願限縮自由與民主體制的權利,來重置與鞏固自我與他人在主流社會中所存在的社會關係與位置。
沒有人希望活在恐怖主義的威脅之下,但是恐懼本身,正是恐怖主義成功的關鍵,也是獨裁政權興起、挑戰民主體制的關鍵。因此,我們需要的,是警戒「恐懼」對民主體系的傷害,以更開放、多元的態度,面對歧異,消弭恐怖主義的種子,而不是以冗長的人龍、以及繁瑣的程序,來「阻絕」「恐怖份子」;我們必須以更複雜的理由分析與說明,取代簡化的故事與社會常規,來看待恐怖主義的興起;我們必須真誠的面對事情的真相,即令它令人恐懼與尷尬。我相信,唯有更民主的體制、更自由的生活,恐怖主義所意圖散佈的恐懼氛圍,才無法得逞,這才是真正消弭恐怖主義的最佳方式。
NOTE
(1)小編註:可以參考Eviatar Zerubavel的著作:「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Silence and Denial in Everyday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中文翻譯:「沉默串謀者—真相,為何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由早安財經出版社翻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