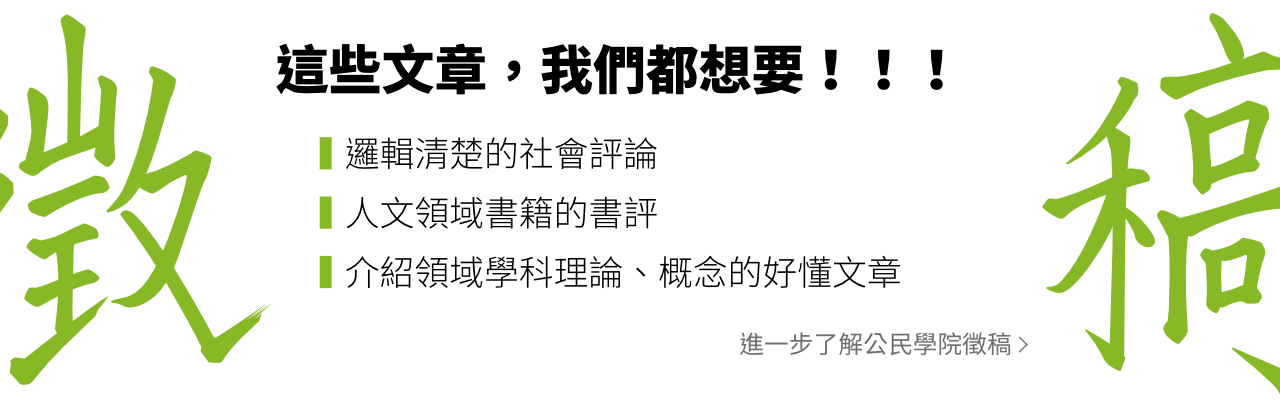圖/陳小冠
圖/陳小冠階級魔咒如何再製:文化與品味的遊戲
在某次的家暴諮商中,輔導員對於某學員阿國說了這樣子的話:
你今天看起來不一樣喔⋯⋯不像以前一樣,髒髒的就來上課。我們學心理學的都知道,人穿衣服的方式不一樣時,說話的態度也就會跟著轉變,人要是穿著乾乾淨淨,語言的使用也會比較有分寸⋯⋯如果你在課堂上都穿成這樣,很難想像你在家會是怎樣?要是穿得那麼隨便,那你說的話是不是就會像你的穿著一樣粗魯,沒分寸呢?
各位是否覺得心理學這麼說,有點道理?大概很少看到穿晚禮服或西裝的人,會嚼檳榔或口出惡言吧。所以是否只要我們穿著比較正式一點,我們的談吐是否也會跟著稍微正式?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其實當天,阿國一如往常,在上課時間準時出現,只是他今天不是從工地直接過來,所以沒有以前骯髒邋遢的樣子,難怪老師會讚美他。但是,人的穿著就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本質」嗎?從工地過來上課,如果沒有回家換乾淨衣服,是否就代表了他這個人「粗魯、沒分寸」?而這樣子透過「穿著品味」來評斷一個人,反映了現代階級社會的什麼問題呢?
以文化形式呈現的階級遊戲規則
不同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階級文化通常都很熟悉,但是對於另外一個階級的文化,不僅不熟悉,而且還經常有比序、比高下的情況,例如上面這位輔導員透過外在服飾的符碼,來評判一個人的文化高低。文化,在當代社會,經常就是用來判斷一個人階級高低的遊戲。
過去社會學在解釋階級的時候,多半都是從個人是否有資本/資產,或者從事哪些職業來判斷,某個人屬於哪一個階級,例如水電工跟工程師就屬於不同階級。不過法國的社會學者Bourdieu說,經濟因素與物質條件,雖是解釋階級差異的最終準則,但階級的遊戲規則,乃是以文化的形式呈現。Bourdieu認為,所謂「好/壞」品味的背後,乃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偏好」,藉此用來區分自己與「粗俗」他者之間的差異,進而鞏固自身的優勢與正當性。例如20世紀引入亞洲、台灣的古典音樂、西洋畫作,都被視為「好品味」的藝術,但是台灣民間吹Si-so-mi的鼓吹,或者幫忙畫遺像的畫師,都不登大雅之堂。
階級污名的烙印是如此沉重,指控不但嚴厲且讓人難堪,導致許多工人階級不願提起自己的出身。英國女性主義學者Skeggs認為,當工人階級女性在面對階級不公的審視時,中產階級受人尊敬的性別展演,則成為她們值得模仿但卻不易做到的因應策略。值得模仿,乃是因為當工人階級女性被(誤)認為是中產階級,就可以不用再背負階級的污名;不易做到,則因要能舉止嫻雅、受人尊敬,先須熟知「正確」的知識,能夠對自己的作為感到自信無誤,乃是中產階級的特質。
然而,工人階級在模仿的過程中,不但要擔心自己畫虎不成反類犬,害怕因露出馬腳而受到中產階級的嘲笑,同時也要顧忌來自於同儕對自身所謂「裝腔作勢」的指責。在這與上(中產階級)跟下(工人階級)的矛盾比較過程,說明了所謂「階級的情感政治」,也解釋了工人階級在面對宰制階級的價值,可能會感到「欣羨」與/或「忿怒不公」。再者,藉由模仿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被污名化的他者,如何憑藉「仿傚」支配者的形象,來彌補自身位階上的不足,同時也讓階級差異的魔咒,不斷複製。
喝米酒,就知道你是下層社會的!
在某次的家暴團體咨商時,輔導員對有喝(米)酒習慣的阿樹(未婚,42歲,待業中,領有殘障津貼)說:「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走路都怪怪的⋯⋯或許你自己主觀認知不覺得,但⋯⋯可以由別人對你的觀察,來客觀的認識自己⋯⋯」,接著他也邀請大家給阿樹建議,大家也紛紛發言。
阿信:米酒便宜嘛,想喝醉但買不起酒的人,都會喝米酒,這種人大腦已經受損了⋯⋯都長期躺在床上,腳都沒有甚麼肉⋯⋯半夜想上廁所,但因喝太醉,或是腳無力,很容易就尿失禁、尿在床上⋯⋯。
阿良:米酒以前都是「蕃仔」在喝的⋯⋯現在很少人在喝米酒⋯⋯。
阿新:喝酒不好,所以我很少喝(酒),但要喝就喝OX,最少也是人頭馬⋯⋯。

從「走路姿勢」真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怪怪的嗎?其實從另外三個學員的回答來看,喝酒並不是問題,而是「喝什麼酒」才是問題。喝高檔的、貴的,就不會有問題,喝米酒就是「蕃仔」、不入流的人。透過物質消費的展示,我們很輕易地就可以去判定一個人的階級身份,而不管此人過去的任何經歷,這就如Bourdieu說的:「宰制階級的『品味』標準,不但『理所當然』成為社會上行事的準則,也用來進一步用來區分自己與『他者』的不同,然而『好』品味背後,乃是階級審視的眼光 。」
就以阿樹的例子來看,,當大家熱烈討論阿樹酗酒問題時,卻沒有人提到阿樹那天上課前剛買了一本《朗文英語字典》,也是在場唯一擁有大學文憑的成員。換言之,階級的污名是如此強大,不但可以漠視阿樹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更因錯誤的文化品味,將他不穩的步伐,連結到「肌肉萎縮」、「大腦受損」,與酗酒之間的關係。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僅是中產專業人士會對他者進行階級的評價(例如輔導員對於穿著骯髒的阿國評價、對於阿樹走路姿勢的評價),階級的評價也會在男性之間不斷進行相互凝視、比較(即使是大學畢業的阿樹,也因為喝米酒而被判定是低下階級)。透過這樣子的過程,特定的觀點成為了有價值的觀點,特定人說的話才算得上是有份量的話。
那麼,那些才是有價值的社會觀點呢?那就是良好的情緒管理,這個是台灣社會宰制階級最為高唱的價值。
「良好」的情緒管理: 實踐中產階級價值
「情緒管理」常常是我們參加心靈諮商團體最重要的課程內容之一,市面上許多的書籍,也都在教導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情緒,達到自我提升的目標。沒辦法達成情緒管理的人,通常會被認為是不理性、無理取鬧的人。
在某次的授課過程中,輔導員透過介紹「現實治療法」,解釋「理性選擇」可以改變個人的行徑。為了提供學員更清楚的圖像,輔導員在黑板上畫一輛車,其中兩個前輪分別代表「認知」與「行為」,而兩個後輪則是「生理」與「情緒」,車子前面則有兩條可選擇的道路,一條是「不再犯(家暴)的光明太陽之路」,另一條是通往「烏雲再犯的報復之路」,意在告訴學員,「如果你願意,你的理智可以掌控你的情緒,就像方向盤可以決定車子前往的途徑,至於會不會再犯家暴,也完全操之在你手裡⋯⋯。」
而依照我們聽到某輔導員的看法,能否成功做到情緒管理,則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選擇:
輔導員:……很多時候……你們(家暴學員)是情緒在前面引導著你……為什麼很多人都跟你們有同樣的情形……可是只有你們才來到這裡,那些跟你們有類似問題的人都走到哪裡去? ……來這裡最大的目的就是藉著別人的提醒來察覺自己走偏了,調整情緒,認識自己,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要能成功的管理憤怒的情緒,就必須打從心理認同情緒管理的重要,不該覺得那只是一種強加在你身上的價值,而是你看待你自己,或希望別人看待你的一種價值……。
似乎輔導員認為,只要是心智「健康」的人,都應該能做到情緒管理;家暴之所以會發生,似乎也說明家暴男性「偏差」的人格特質與不健全的心智。學員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老師們最大的問題是⋯⋯老覺得我們心理有問題,老是想要治療我們⋯⋯我們一說話時,便指著我們鼻子罵說我們說話的語氣還帶有著恨⋯⋯。」

心理諮商不只是中產階級用來建構理想自我的手段 ,它也利用自身所熟悉的語言,提倡高人一等的(階級)價值。透過心理諮商的衡量標準,中產階級便容易成為情緒管理的模範生,不但具備良好的自制力,也能成功抗拒社會的不良誘因;反觀工人階級因(被中產階級認為)心理層次貧乏,自然也就無法擁有情緒管理的特質,除了像小孩一般衝動、「易受(外界)影響」,鄙俗的文化也需要再教育。
然而,工人階級「低下」的文化實踐,卻是中產階級價值得以存在的條件;唯有透過他者粗魯過露的情緒表現,才能襯托自身優雅、自制的情緒展演。看見中產階級 (理想) 的人格特質,並不等於說明工人階級人格的必然缺陷;但透過階級的不公凝視,工人階級的文化習性,卻被用來解釋他們情緒管理失敗的原因,「鄙俗的」情緒場域,造就了工人階級薄弱的道德感。再者,能在遭遇困難時,不慌張失措、不輕易動怒,可以從容不迫的處理問題,被看成是屬於擁有許多成功經驗人士的特質,但是如此「優雅」特質的背後,其實是需要有資本支持的。
當我們透過情緒管理的能力來決定人格特質的好/壞時,我們就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差異,歸究到是個人的個性、能力缺失(例如輔導員一直強調的,要參與輔導課程的成員,必須理性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漠視其背後所經歷的結構困境(忽視了勞工階級遭受的經濟困窘壓力),也忽略了需要更進一步挑戰「情緒管理」乃是中產階級價值的委婉代名詞。
階級關係是動態的
那麼如果有一個人,他的職業是經理,也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那麼他是否就必然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呢?這裡我們必須說明,「階級化」乃是「相對比較」的過程,必須看此人,在什麼樣子的社會情境,透過跟誰比較的過程,才能被確認是屬於那個階級,換言之,「階級關係」並非是靜態的,而是會因對象與場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阿忠(分居中,49歲,外商公司主管)與其他成員的確很「不一樣」。首先,阿忠是輔導員眼中對自己外表「負責」的人。每次上課,阿忠總是衣著乾淨整齊,Polo衫搭配休閒長褲。除此之外,阿忠曾在美國拿到碩士,從小家庭環境相當不錯,如同他建議:「在我們那個年代,要能到美國念個碩士,除了自己要很認真外,家裡一定也要能支持
⋯⋯」。
阿忠不太擔心被誤認為沒有用的男人,他成功的過去也弭平這類的疑慮。他很清楚這種自信與特質:「別人對我的印象是⋯⋯我有當主管的那種特質,就是要很認真,或者是要有自律性的那種特質⋯⋯其實我當主管那麼多年,甚至在菲律賓,我都不用打卡,原則上,我不需要⋯⋯」。
阿忠每次都很有技巧地陳述自己的意見。譬如,不像阿春每每情緒激動抱怨家暴法是「惡法」,阿忠在批評家暴法的不公時,懂得不偏頗地提供例子說明,輔導員就評論說:「因為阿忠受過的教育與學術知識,讓他在說話時,可以很有條理的把事情說清楚,也會比較公正、讓人接受他的意見,做到有效的溝通⋯⋯」。再者,當阿忠發言占去過多時間,或情緒過於激動時,他也會以通情達理的口吻說:「抱歉我又講太多了」或自省的說「我這邊說話太過激動了,真是抱歉」,也因此「合理」讓大家繼續聽他說下去。
然而,讓人欣羨的階級展演,有其場域上的限制。例如只有高職學歷的小張,雖然經濟條件很好,但是當他要模仿高文化資本的人時,有時候就會露出馬腳而受到挑戰。譬如當他企圖在課堂上引用韓非子時,他也問其他學員:「韓非子你們知道吧⋯⋯孔子的學生,那本書我看了一年多⋯⋯」,這時阿忠馬上質疑:「韓非子是孔子的學生嗎?」。又,當小張用畫家的比喻解釋櫻花樹的生意時,同時也告訴我們:「⋯⋯你們知道那個叫『泛德』的畫家, 來自產很多鬱金香的國家」,其實他是指梵谷。換言之,小張雖想藉由挪用文化資本,讓自己說話更有份量,但在挪用的過程,即便知道階級的遊戲規則,卻因對場域的不熟悉,仍會不經意犯規,因此可能落入「裝腔作勢」的窘境。

中產階級的阿忠,在文化資本的挪用過程中,一樣有場域上的限制。譬如,當阿忠試著向檢察官解釋,不是他故意違反遠離令,而是他必須到妻子住處接小孩和繳交大樓管理費時,檢察官並不採納他的說法,反而諷刺地問:「你書念那麼多,連字都不會看嗎?」。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法官不但輕易漠視阿忠個人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也因更因家暴的發生,質疑阿忠中產階級的正當性。中產階級的特質,雖讓阿忠在小團體裡如魚得水,贏得大家尊敬,但同樣的階級特質,卻在法庭上成為讓人詬病的把柄。阿忠也意識到家暴對自己的影響,即便他擁有不錯的事業與學歷,但只要被冠上家暴,就像隻被去勢的公雞,淪為別人眼中的笑柄。透過階級的「排外/排壞」條款,中產階級男人不會家暴,如果男人會家暴,那他一定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在否認阿忠階級屬性的同時,中產階級也繼續保有了自身的「純淨」。
開展工人的階級文化論述
階級的遊戲規則,是透過文化差異來呈現,不同階級的人,因為對於不同文化場域並不熟悉,因此要挪用該文化時,自然有其侷限,例如連勝文或馬英九要假裝跟菜市場攤販很熟,從他們的動作表情就可以看到其扭捏作態樣貌;同樣地,要一個從小聽台語流行音樂的人,某天晚上正襟危坐在國家歌劇院聽華格納「飛行的荷蘭人」,恐怕幾分鐘就會睡著吧!但是為何我們覺得某些文化就是比較有品味?比較高級呢?不要忘記,這些品味的比較,其實都是人為的,品味有高低之分,這根本就是個神話,而「神話就是把人為的事物變成是自然的」!
三位作者之一(猜猜是誰?),在他高三的時候,跟朋友去吃港式飲茶,那是他第一次吃飲茶,吃完之後、付了錢,櫃檯找了2塊錢,當時他突然心血來潮,想到電影裡頭的有錢人都會給小費,因此就留下這兩個銅板給櫃檯小姐,說要當小費,結果櫃檯小姐笑的花枝亂顫,口中念念有詞「小費2塊錢」。階級的污名化力道如此強大,使得不熟悉支配階級文化的人,雖然要努力倣效,但卻也經常落入露出馬腳,裝腔作勢、假仙的窘境。
這個階級(文化)再製的魔咒如何打破呢?過去十幾年來翻轉「台客」、「本土藝術」的意象跟論述,就是很好的例子。唯有工人階級自己發展出自己的階級文化論述,才有力量來對抗宰制階級所設下的品味標準,進而改變不平等的階級(文化)關係。
NOTE
- 本文改寫自三人合著的文章:「男性家暴者的諮商經驗:階級差異如何再製」,台灣社會學刊,2014,第55期,頁22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