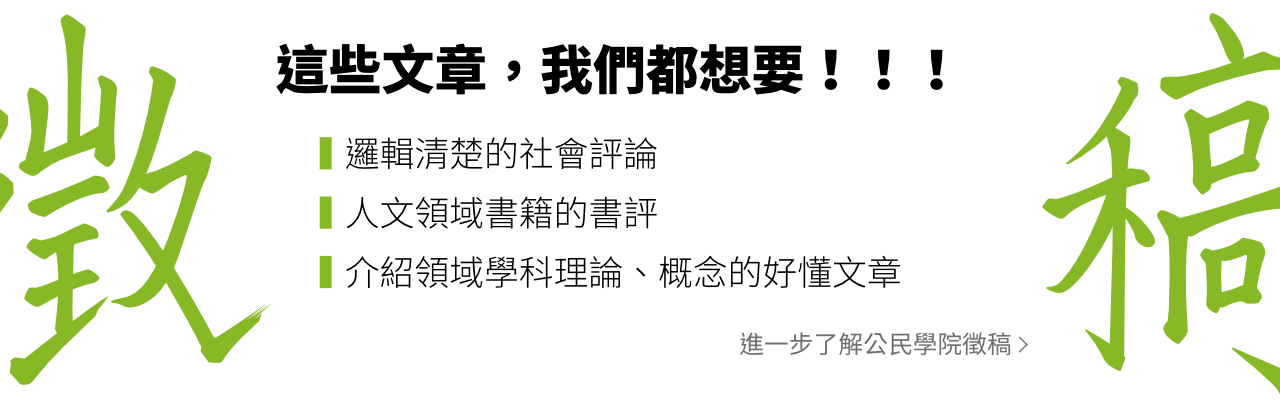圖/陳小冠
圖/陳小冠老屋.消費與集體記憶
一九九○年代末,台灣各地慢慢開始出現了一些「老街觀光地」,這些清領或日治時期以來的舊市街被重新修整後,像是三峽老街、淡水老街、大稻埕、安平老街等,都不負眾望地吸引了相當多的人潮。同時,自二○○○年代中以來,從之前以一個整體街區為主的聚集性經濟發展,轉向為單店的發展,改造老屋的消費設施更成為一種流行,從南到北,老屋咖啡、老屋民宿、老屋藝廊如初春新生的綠芽,遍佈全台,其中台南的林百貨的更生,更是老屋復活的象徵性指標。人們到爐鍋咖啡、南街得意、宮原眼科、正興民宿咖啡,也許是特地去觀光,也可能只是日常午後的一段休閒,「老屋」的意象成了台灣人心中一個可以被消費的理想像。這在九○年代以前,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
「老屋」,其實是一個曖昧的形容,在樣式上有宿舍、洋宅、民家、三合院,內裝上亦常是各時代的氣息混雜,像台中的目覺咖啡三店,外觀保持了日治時期的舊貌,內部裝潢卻展現著現代主義的風格。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老屋」並沒有一個準確的判斷基礎,雖然大多數的「老屋」指的是至少屋齡超多五十年——尤其是日治時期——的老房子,但呈現出來的不必然是某一個時代的還原,反而常是由不同時光的象徵交錯拼貼成的意象。

如同英國學者John Urry所說,消費者在觀光時所消費的是「想像的」對象,一種在視覺上所能得的「表層的現實性」。在「老屋」裡,消費者不需要明確分辨出各種時代的象徵,而是在與現代的日常相對的老屋中,搜集多樣與自己想像的「老屋」對應的文化符碼,形塑出一種與歷史相連的、懷舊的連續感,重要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元素,而是能被辨識出來是「古早」的符碼。因此,在滿是現代主義風格的老屋咖啡中,享受著「這是間老房子」、「地上保留著磨石子地」的驚喜,而不在意桌椅是否是同時代留下的產物;在日治時期建築的老屋咖啡裡看到大同寶寶,與其說感到錯置的突兀,倒不如說是童年回憶的召喚。被消費的不是「真實的」古早、不是腐朽的陳舊,而是分享了「老」的意象:老房子、老地板、老式裝潢…那些在台灣被經歷過的曾經。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老屋」消費的重點在於被視作「老的」、「古早的」氛圍。但是,一九五○年代以來作為台北著名藝文之地的明星咖啡,呈現著古典歐風,而秘氏咖啡展現的是一九二○年代上海十里洋場的奢華,它們都具備了古典元素,但卻鮮少被納入近年來討論「老屋」的範疇。因為,這一波「老屋」、「老街」意象的中心,是「過往的台灣」,在「老」的符碼之外,必須再加上「台灣」的意象,才是九○年代末以來「老」風潮所消費的意象。

以文化消費學來說,人們在進行消費時,也在進行一種認同的建構。當消費者選擇了欲望指向的對象時,也就是在選擇能展現自我的表徵。如同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所說的,品味是一種社會銘刻在個人身體後的展現:透過我過去生活的經驗、感覺、社會歸屬或地位的總結,我選擇了這個而不是那個,這其中就意味了這個而不是那個被我當作了我的個性的代表,是我對外在世界發出的獨特的訊息。消費的對象,即是我的理想像的投射。這種主體投射的作用在文化消費上尤為明顯。我們只是想喝咖啡時,或許會選擇麥當勞或全家便利商店,但是,在想享受一個悠閒的午後時,大約不會去找一間與自己的品味完全不合的咖啡館,就像喜歡《進擊的巨人》裡的兵長的人,不會在手機上掛上其他角色的吊飾。
換句話說,「老屋」風潮顯現出的,正是「台灣」被視作了一個理想的形象。在九○年代末以前,大眾文化裡呈現出的理想像,是中國的、架空的、歐美的,而台灣,始終不在場。言情小說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九○年代中台灣言情小說剛出現時,總是古裝劇、或是沒有實際可辨識的架空場景,台灣漫畫亦然。直到九○年代末,在台北的中山北路或東區逛街,在花蓮的金針花園間相遇,成了言情小說中的浪漫表徵,「台灣」開始擁有承載得起文化想像的美。
這種轉變也呈現在「老屋」風潮的興起中,「老屋」店家不只是讓台灣作為一個理想像的承載符碼,更進一步來說,從「老」的意義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消費者不只是在追求「台灣」作為一個現在的理想像,更在其中尋求與過往歷史經驗連結的連續性。

長期以來,在國民黨的教育體系中,台灣的存在被附屬在中國之下,甚至被抹消,戰後世代在教育與媒體體系中所習得的,是Pierre Nora所謂的義務性的記憶,也就是虛像的、不曾被經驗過的「中國」。台灣的經驗與歷史,只能透過身體的記憶與被壓抑的集體記憶傳遞下來。在那個時代,台灣與「理想的形象」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也因此,「老街」、「老屋」潮在九○年代後半興起的這個時間點,具有相當微妙的意義:並不是一九八七年解嚴了,人的意識就得以自由,文化的積累不是一蹴可及,一直要等到經過十多年的醞釀,以台灣這塊土地為中心的集體記憶才慢慢建立起自身的立足點,人們開始相信以台灣作為自我起源的開端,並不會因此讓共同體失去偉大的榮光──在過去,我們總被教育著「數大就是美」、「愈古老的愈偉大」、「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是四大文明之一,是一切的源頭」,而相對的,小的=年輕的=低劣的的想法就被視作當然地灌進了人們的意識裡。從這個脈絡來看,「老屋」風潮正展現了台灣人以自身為中心,站在自己所在的土地上,追尋自身過去起源的意義。
一九七○年代以來,從中國化政策的打壓底下掙扎著浮出地表的「台灣」,總與苦痛的象徵連結在一起,唯有透過這樣的象徵,才能凝聚被壓迫的一方,與支配者對抗。而在二○○○年後,「台灣」的意象開始具有可以作為「理想像」的正面意涵,這並非表示台灣歷史中的沉重就此被遺忘,而是顯示出台灣從可視、到被正視、以及認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