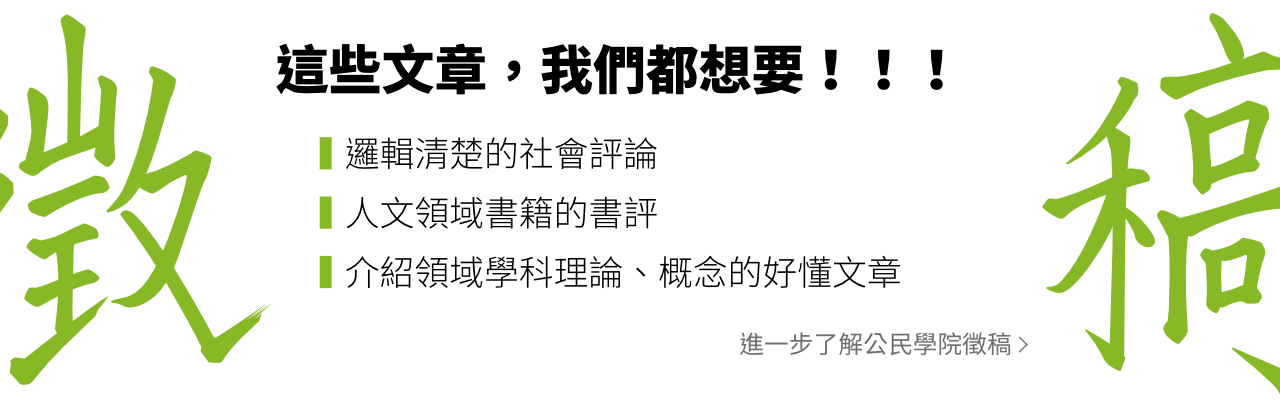圖/陳小冠
圖/陳小冠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的二十一世紀史學新思維--瑞典國立歷史博物館怎麼做?
現代史上,逞強的男性出了什麼事?
2014年,轉眼走到了年尾。從台灣來看,今年發生好多事。從三一八學運到餿水油風暴,以迄目前仍在激烈論辯的性別平權與多元成家法案。雖然時序近冬,但台灣社會還有許多攸關未來發展的重大事件正在進行。大家似乎並不打算讓2014年再如過往幾年那樣,只能無奈地任人偷走。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今年也是歷史上重要的一年。有些事與台灣自身處境相仿,受到許多關注。例如,蘇格蘭在九月舉行了三百年來第一次住民自決公投,以及目前仍在進行的香港佔中行動。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因與台灣沒有太直接關連,以至於我們的學界或媒體並沒有給予同等份量的注意。例如,烏克蘭危機與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紀念。

在歐美,重新檢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可說是今年史學界最重要的議題;而相關的論述,也經常被與當前的俄國情勢及烏克蘭危機放在一起討論。這兩年來,透過許多專書出版,西方學界對一戰爆發的經過做了與過往大不相同的檢討,也帶動了更有啟發性的詮釋觀點與討論問題的態度。
大體而言,有別於以往將戰爭責任完全歸咎於德國,一百年後的今天,歷史學者更傾向於去檢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會爆發,當時的歐洲五強(英法奧德俄)究竟是如何在互動?以這兩年出版的眾多相關新書中被最高度評價之一:劍橋大學歐洲近現代史教授Christopher Clark 所著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何以邁向戰爭之路》(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為例,Clark就指出,不應以找出代罪羔羊的詮釋方式,包裹式地解釋一戰的發生。他認為,一戰的爆發,並非肇因於同盟國與協約國兩個敵對陣營互相挑釁的結果。反之,兩個陣營都是非常脆弱的結盟。根據統計,盟友之間簽訂的白紙黑字協議,被履行的比例大概只有25%。在爾虞我詐的氛圍下,表面上同陣營的人,互信基礎極為薄弱,誰也不敢確定所謂的盟友到底是敵是友?而正是這種深切的不確定感,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Clark在閱讀大量書信、備忘錄與回憶錄後發現,當時主宰歐洲政治的男性(全都是)在決策時,幾乎陷入同樣的性別文化思維框架,經常使用類似的語彙來描述自己面臨的困境。他因此提出一個概念:「強逞男性雄風所引發的危機」(crisis of masculinity)。雖然一些書評對這個概念並不完全認同,但是,Clark的用意卻是想藉此指出,1914年歐洲五強領導者,雖然各自對當時國際情勢做過所謂的理性權衡與評估,但最終卻因難逃本位主義,更擔心自己若不硬撐出強者姿態,隨時會有顏面無光的危險。結果就紛紛像被無端夢寐所牽引的夢遊者般,雖然自認處處小心,但卻在無法看清前路的情況下,讓國家捲入戰爭的泥淖。
Clark提出「強逞男性雄風所引發的危機」這個概念,是有感而發的。對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盲昧逞強的狀況下爆發,Clark 在出書後受訪時,不斷提出警告。 1他認為,目前我們所處的世界局勢,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那樣。而喜歡逞男性雄風的政治人物,就像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那樣。在Clark看來,普丁在心態上還活在十九世紀的男性統治者性別文化想像裏,許多方面都只想靠逞狠鬥猛來維護自己的強者/強國尊嚴。
強逞男性雄風出了什麼問題?Clark並非認為懦弱、意志不堅的政治領導人是好的。他書中所指的那些喜歡誇炫陽剛之氣的掌權者,問題出在,為了顧全自己的顏面,不斷用硬撐、硬拗的偏執手段,掩飾個人意志上的軟弱,以讓大家相信他的確是個「勇者」,而非「懦夫」(in an obsessive desire to triumph over the ‘weakness’ of one’s own will, to be ‘a person of courage’, […..] rather than ‘a person of fear’.)。 是這種性別文化的意識牢籠作祟,讓男性決策者假理性之名行事,但卻越來越往意氣用事的方向暴衝。而且當重大問題發生後,並無法放下身段圓融解決。
從「性別」觀點看世界史與個人,在歷史詮釋上,並非新的。然而,過去的作法比較放在女性主義思維對男性宰制現實的抗議與抗衡上(例如《女人的世界史》一書);在大眾媒體呈現上,也比較傾向於女性在世界大戰期間默默承受的苦難(例如日劇《櫻子》)。Clark論述一戰爆發經過的切入點,卻是跳脫傳統「父權思想」與「女性主義」對立的二分法,改從男性如何陷入男性自身的性別意識牢籠,以至於思考底線變成不願意「輸人輸陣」。但卻因此讓自己身陷困境無以自拔,最後連整個國家與世界都跟著捲入世界大戰的悲劇當中。
從歷史研究角度看「男人真命苦」?
「男人真命苦」是很多成年男性的口頭禪。然而,二十一世紀可不可以讓這樣的悲嘆消失?
重新看待性別議題,不只是學術研究的問題,也牽涉到二十一世紀如何突破十九世紀留下的「國族主義」思維。「國族主義」基本上是架構在父系繁衍基礎上的思想,強調具有一定血緣關係的人,就是種族文化的承載者,因此也必須成為繼續傳承共同文化的行動者。國家被想像成一群在父系血緣關係上,有一定程度連結的種族共同體;而且,為了延續種族永續存在的「神聖使命」,有血緣關係的人,不管意願如何,絕對不可彼此分離。
然而,現代學術研究卻清楚告訴我們,所謂「種族」或「民族」,其實只是想像的共同體。2在古代,即便是生活在相近地區的人,也不能直截了當論斷,他們一定就有近親血緣關係。也許因為貿易接觸或交通往來,他們的語言產生一些互相影響的現象,甚至有所謂「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的出現。但學者並不能因此就證明,這些使用共通語言的人群源自同一祖先;或是同一祖先對這些上古人群而言,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在現代考古學家對早期日耳曼文化研究上,處處可以見到,在詮釋與推論上的小心謹慎,不讓過去建構在古羅馬父權主義思維上的傳統認知,繼續理所當然地宰制現代學術研究。3

古羅馬思想傳統,不就是西方的傳統嗎?喔,喔,這真的要小心!我們的教科書在這方面錯得還滿嚴重的。就像漢族文化並非中國文化的全部,更非台灣文化的全部。別忘了,歐洲原來也是各種原住民居住的世界。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去年有一個台灣也有報導的有趣新聞:〈考古大烏龍:王子其實是公主〉,4就是義大利考古學者拿古羅馬的性別文化觀來詮釋伊特拉斯坎人(the Etruscans,義大利半島另一個原住民部族)的墓葬,結果把長矛視為男性文化象徵物,珠寶視為女性文化象徵物。經過骨質分析,卻發現完全錯置了。

西方經過二十世紀上半葉種族主義帶來的重大災難,近幾十年來教育努力的方向,就是擺脫國族主義帶來的遺害,強調公民社會的多元價值。今年九月,蘇格蘭公投採取住民自決原則,而不採取血緣認定原則,就是相當值得注意的成就。
當瑞典人不再以勇猛的維京人後代自居......
今年暑假,筆者在瑞典進行短期考察研究,剛好遇上斯德哥爾摩的國立歷史博物館(Historiska)舉辦維京特展(Vikings)。5這個展覽的策展出發點,簡單講,就是要破除瑞典人是維京人後代的「血緣臍帶想像」。換句話說,透過這個展覽,瑞典國立博物館想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作為現代國家,瑞典追求的價值,並非建立在國族主義之上。而且不要忘記,瑞典真正的原住民是Sámi人,而非所謂的維京人。

斯德哥爾摩這個維京特展開宗明義告訴觀眾,所謂Viking,是一種遠洋出海討生活的「行業」,而非「人種」。史書常將西元700-1100年間的斯堪地納維亞歷史稱作「維京人時代」,並非正確的標籤。當時斯堪地納維亞地區大部分居民其實是農民、獵人、手工匠,而非遠洋出海的「維京人」。即便比較常出海做貿易營生的北歐人,也不是一年到頭都在海上go viking,而是有時也會回家耕牧做農人、或做手工業。換言之,從國族主義的角度,將現代瑞典人、丹麥人、挪威人視為維京人後代,是有相當大的誤解。應該說,這四百年間,斯堪地納維亞的居民,有時會出海去當Vikings,而整體來看,這些人在歷史上確實的行徑作為,也非都是那麼勇猛、所向披靡。
當然,這樣的誤解其來有自。因此,展區的第一部分便展出十九世紀以來的一些海報與圖像,告訴觀眾,維京人的概念是在十九世紀末為了順應歐洲當時風起雲湧的國族主義思維,才在短時間內被強力建構起來的。自此直至納粹時代,這個概念不斷被有心人操弄,以為不同的威權政治文化服務。

考古實物配合實景模型與嚴謹製作的多媒體影片,這個精心規劃的展覽從生活與社會文化各層面,深入介紹維京歷史。然而,最令筆者驚豔的,更是在走出特展展場後,前往史前史常設展的銜接通道上,與另一個精心安排的思考區相遇。

進入時空任意門:瑞典博物館教育如何關心性別與家庭議題?
銜接通道上,一塊說明板讓我停下腳步,靜靜細讀起來。越讀越感動。
說明板上寫著:「你剛從維京特展出來,對那個時代而言,『出外』與『相遇』是重要的事。或許你已發現,當時的人與現代人的差別,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許多我們現在會問的問題,當時人也在問。例如『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你正站在一個銜接通道上,在一個時空之旅的旅程中稍事停歇。每一扇門上都有一個任何時代的人都會問、對歷史上所有的人都重要的問題。這部分的史前史是根據這些問題組織起來,但也是有關歷史知識如何借助考古學幫助而建構起來的。」

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有哪些?
第一個問題【你從哪裡來?】:「是上帝創造的?是從別的動物演化來的?還是如北歐神話與許多千年前的雕刻所顯示,與麋鹿、海豹及水禽連結在一起的創生起源有關?」

第二個問題【你往何處去?】
看板上寫的內容很有思考引導性:「出外旅行時,我們跨越不同的邊界。今日所見的邊界,古時並無,這些也非絕對或永恆的邊界。有資源、也有機會的人,帶著好奇心環遊世界,認識世上萬物以及過往沒有學過的東西。但是當難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彼此陌生雙方的遇合,卻往往不令人那麼興奮。這個銜接區展示的,是過去旅人出外時留下的印跡,以及人與人遇合時的一些見證。【…】今日的瑞典是經歷無數出外探尋與遇合後所得的結果。希望透過這個銜接區的展示,你開始有興趣去省思自己的世界觀,省思生命、他人與你自己。」

第三個問題【你的世界有多大?】:「地平線的彼端是什麼?區隔『在家』與『離家』的界限劃在哪裡?你心目中的世界長什麼樣?未來看起來可能會如何?是你的責任嗎?」

第三個問題【你的世界是以什麼方式組織起來的?】
入門處看板寫著:「這些東西是誰的?博物館為何用這種方式展示?東西如何被分類?這樣的分類方式如何影響歷史?」
另一個看板則提出進一步的思考引導:「你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歷史嗎?考古學家創造了史前史,並將之整理分類,以典藏圖錄記載之。博物館的典藏與展示,正反映出博物館外的世界如何看待這些文物。我們目前所認知的各種疆界,在史前時代並不存在。然而,在我們的庫房裡,這些被發掘出土的文物,卻依發掘時所屬的現代行政區域與教區被分類典藏。我們依照不同的分類標準來展示一些典藏品。這樣的分類方式可以達到什麼目的?會影響到我們的詮釋嗎?」


第四個問題【誰在述說關於你的歷史?】
入門處的看板寫著:「我們該將歷史運用在哪些地方?歷史能提供我們觀點來理解『今天』嗎?誰有權支配歷史?」
另一個看板則寫著:「同樣的文物或同樣的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展示。關鍵在於,由誰來述說這個故事?今天有一些群體利用歷史強化他們的認同,史前時代的群體認同是什麼樣子?活在現代的我們有辦法發現並了解其中的運作嗎?試圖透過史前史研究來追溯不同文化的源流,這種研究法是否可行?或者是重要的?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第五個問題【宰制你生命的是什麼?】:「誰決定你該做什麼?上帝?市場?外力?家人?或是你自己?目前的情況是你所願的嗎?為了達到你想要的,你可以捨棄什麼?」

第六個問題【你是誰?】:「你怎麼看自己?別人又怎麼看你?何謂『人類』?不同時期的畫像對身體與臉部表情的刻劃非常不同。人們特別希望擁有哪些特質?大家會選擇展示哪些部分?是誰在決定哪些部分該被展示?我們常透過與動物互相比較,來定義人類是什麼。但我們卻也用動物的特質來形容某些人類的性格特徵,或有時拿人類的特質來形容動物。」

最後一個問題【你跟誰同住?】
門口的看板上寫著:「何謂家庭?誰決定什麼叫『正常』?什麼叫『不同』?何謂男性?何謂女性?從何時起可以說一個人成為成年人?」
另一塊看板寫得更有啟發性:「爸,媽,孩子,這種家庭觀存在於史前嗎?所有人都是依照這種模式生活嗎?現代社會還有多少人是按照這樣的型態在生活?我們所在的社會決定了何謂『正常』。我們是否知道,那些無法配合這種理想模式的人,到底如何生活?在史前時代,每個人都被社會接受嗎?何謂男性?何謂女性?從何時起可以說一個人是成年人?我們今天的價值觀是否影響到我們對這些史前文物的詮釋?」

建構多元性別文化,讓我們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點
瑞典國立歷史博物館不算是歐洲觀光客熱衷朝聖的博物館。今年夏天他們卻以深具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推出一個讓參觀者可以靜靜檢視歷史知識與個人認知關係的美好展覽。這個策劃得極為用心的展覽所提供的,不是國族文化意識形態裡的「黃金時代」;反之,卻用深具啟發意義的提問,鼓勵觀眾看過展覽後,自己進一步思考,歷史學與考古學作為建構之學,在詮釋上,可能產生的盲點;而我們又該如何警覺這些盲點會出現在何處?
令人讚賞的,也在於這個展覽傳遞的訊息:國家並非由同一祖先的後代建構起來的,而是不同人群遇合後一起攜手打造出來的結果。在這樣的認知上,瑞典國立博物館放棄十九世紀國族主義看重的課題,不再認為明確去定義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根源是必要的事。反之,他們放棄傳統思維框架,不再以維京人自居,不再陷溺在彪悍的海上武士歷史迷思裡;更不認為男性雄風所追求的強者形象,是自己國家文化需要看重的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對建立符合人性社會真正的關懷。他們認為,生態環保、民主多元、性別平等、尊重人權等普世價值,才是一個健康的國家在永續發展上應該追求的目標。
僵化制式的性別文化觀不僅讓生理上不是異性戀的人,長期以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與歧視;僵化制式的性別意識型態牢籠,有時也讓一些自認為是「正常人」的人,給無數無辜的人帶來世界大戰的摧殘之苦。
性別文化平權的多元建構,不只是法律權利的問題,其實也攸關到世界和平的建構。
如果男性不再被要求時時要能擺出輸人不輸陣的「男性本色」,女性不再擺盪於電影《窈窕淑女》裏的奧黛麗赫本與唐代武則天兩個極端之間,大家共同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點;也由此出發,在理解異性的同時,也接納傳統「男」與「女」狹窄定義下所沒有照顧到的其他性別。如此一來,我們不僅幫助處在困境中的人走出枷鎖,我們更接納了自己。大家重新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點,互相善待,而不再一起作為傳統性別文化觀宰制下的被綑綁者。
NOTE
(1) 相關訪談參見:http://www.npr.org/2013/04/23/178616215/stumbling-into-world-war-i-like-sleepwalkers; http://theglobalobservatory.org/interviews/707-are-we-sleepwalking-towards-war-interview-with-chris-clark-.html.
(2)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出版,2010 年)。
(3) 相關研究介紹參見: http://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11262.
(4) https://tw.news.yahoo.com/考古大烏龍-王子其實是公主-000618744.html.
(5) http://www.historiska.se/home/exhibitions/vik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