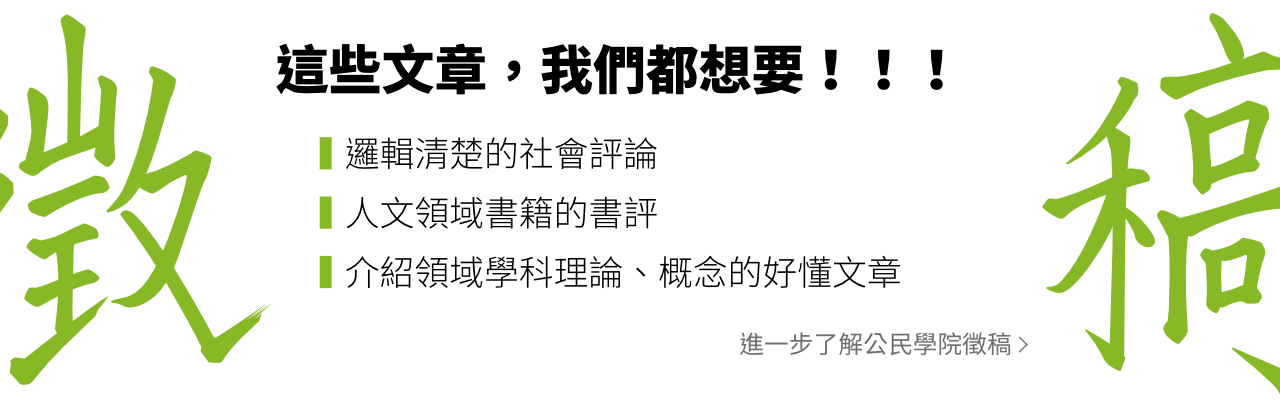圖/陳小冠
圖/陳小冠日記與歷史
每個人或多少都曾經有寫日記的經驗,日記似乎是個人生命的記錄與證言。不過,史學界對於將日記做為歷史研究的材料,一直存在著正反兩面的意見。贊成者認為歷史人物的日記多半會記載當事人對於事件的第一手記錄,因此最接近歷史事實的真相;晚近文化史研究取徑興起,日記也可提供史學家探究小人物的心境、日常生活、人際交網;女性史研究者亦十分注重日記,蓋大敘事的歷史往往不見女性蹤影,唯女性日記能勾描女性自身的生命歷程。反對者則以為即使是事件當事人,也會因種種私人因素而未必將所見所聞在日記中和盤供出,或者即使記載,也多少帶著當事人的偏見而扭曲了事實;反對者也以為文化史、女性史所珍視的日記內容,不過是雞零狗碎之事,無經國濟世之用。儘管意見紛歧,但將日記適當地使用,仍然是大多數史學者所同意。
中國近代史領域裹有所謂晚清四大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和葉昌熾的《緣督盧日記》,後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陸續出版了王世杰的日記,而大陸近二十年更不遺餘力地整理出版許多著名史學家的日記,如胡適、顧詰剛、吳宓;或者地方士紳冷眼觀察世變的記錄,如劉大鵬等,晚近則是蔣介石的日記最引人注目。在臺灣史的領域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更不遺餘力地徵集收藏日記史料、組織日記解讀班,將解讀成果出書發表,也活力旺盛地舉辦了多次的日記研討會和展覽會,將註解、研讀日記的成果公諸於世,一方面讓更多讀者了解日記,另一方面則是吸引私藏日記者能現身捐獻,日記的重要性乃日益受到學界及一般大眾的注目。一時間,原本在夜闌人靜或曉色微光中伏案振筆,刻劃自己每一天的故事,也原本只打算寫給自己觀看回覽的人生,現在藉由無遠弗屆的網路,可以讓不知不識的讀者一覽無遺。這也引發了日記「公/私」屬性的爭辯。一般人均會認定日記乃記錄個人私密經歷與心情之物,不過,也有些人的日記,被認定是為了他人觀看而寫,未必是私密真情的忠實告白。然而,不論公也罷私也好,也不管私密真情才是真實,公開暴露自己種種(有如今日的FB)恐為偽作,日記所記載的內容,就是歷史嗎?
E. H. Carr在他著名的《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一書中認為:過去所發生的事,必須被歷史探究者取擇之後,才會從事實的大海中搖身一變,成為「歷史事實」,而德國著名的社會史學者Jorn Rusen也提出,過去所發生的事要能成為「歷史」,必須是這些事能對現今的狀態、情境或環境構成影響,以及為了追求未來方向而在尋求在過去具有重要性的事物1; 亦即,過去的事要能成為歷史,必須與「現在」有密切關係。此外,過去的記憶也與所謂的「歷史」不盡相同,尤其是十九世紀科學化的歷史研究出現之後,強調以事實證據為基礎、探尋事件因果關係、追求人類整體發展線索為目標的「歷史」乃與多變曖昧的「記憶」(尤其是個人記憶)分道揚鑣。唯1980年代起新文化史崛起後,日記成為微觀歷史的好材料,日記的重要性才又受到青睞。
那麼,日記記載的內容是否合於上述的概念?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幾個層面。一是:日記主人書寫日記時的「現在」是什麼?二是:做為閱讀日記的我們所面對的「現在」又是什麼?這是兩個基本卻又極為複雜的問題,在這篇小文章中,我只打算先探討第一個層次中最物質性的問題,日記主人在什麼媒材上寫日記?
最近高雄師範大學的吳玲青老師即寫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討論此事。2她爬梳《臺灣日日新報》中的廣告、記事,並比較現藏於中研院臺史所以及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日記原件,讓我們得以了解現今所保存的日記,以及日記主人身處的世界,其實是一個日記逐漸「商品化」的時代。以日本東京博文館這家書局為首所發行的制式日記為模本,引領了無數其他書局、出版社、公私行號單位紛紛印製、發售五花八門的日記,除了博文館外,新潮社、平凡社、富山房等知名出版社,發行雜誌的婦人之友社,甚至製造牙膏的「ライオン齒磨本舖」以及賣味精的「味の素本舖」也加入戰場,好不熱鬧!競爭日益激烈之下,為了開發客源、迎合或甚至創造需求以攻佔市場,日記的供應商更挖空心思,設計出不同開本、印工、功能的日記,以滿足(甚至創造)「個性化」的日記書寫需要,於是乎,除了基本款的《當用日記》外,還有各式名目的產品,如適合隨身攜帶的《懷中日記》《ポケット(pocket)日記》,給家庭主婦的《家庭日記》、《婦女日記》、《主婦日記》或給年輕女性及女學生的《令女日記》,給學生用的《小學生日記》、《學生ダイアリ》,意圖開發心性提升氣質的《修養日記》、《文藝日記》、《自由日記》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燎亂。日記本的內容也多半呼應名稱所欲指涉的特色,除了供人記事的空間外,還會附上一些符合日常需要的設計,如家庭主婦的日記會有一些處理家務的資訊和帳簿,學生日記則會提供古今詩文、格言、歷史事件、年表等。3於是乎,日記本超過了單純記事的功能,還加上了許多針對不同身分人所需的日常資訊,其目的也在吸引不同類型的購買者。
這些日記的價格從適合學生購買力的10錢到裝禎印工講究要價1.20的「綾革本」,平均一本日記大概是40-60錢不等,這種價錢對於月入大約是17-40圓的公學校老師而言,其實並不算太便宜,不過,林獻堂夫婦及黃旺成等人均長期使用博文館出品的《當用日記》,林獻堂夫人楊水心女士或高慈美則時或使用主婦之友發行的日記。然而,也有些長期寫日記的人並未加入這個日記商品化的行列,有人願意自費印製符合自己需要的日記本,如張麗俊; 也有人就地取材,拿身邊最方便之物來書寫,如楊英風多用活頁紙,吳新榮則取自家診所的筆記本書寫。
記載每日事媒材的討論,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推㪣日記書寫時可能面臨的情境。使用商品化、制式化的日記本,多少會受限於它所提供的每日一頁的書寫空間,日記的內容就不能雜亂散漫,多會挑選自己認為值得記錄之事,以免逸出制式本限定的空間。當然,未必每位日記主人都一板一眼乖乖地就範於日記格式,忠於界限與脫逸框範之間,看得出日記主人的性格。就我有限的閱讀所見,林獻堂即是一位謹守範限的日記主,他的日記少有跨頁至隔日者;黃旺成最初的日記,充滿了年輕熱情與希望,每日記事內容很多,但一、兩年後,熱情漸失,日記內容日漸縮短。像詩人如吳新榮、張麗俊,或藝術家楊英風,大概不喜約束,因此寧願在沒有空間限制的本子上馳騁自己的快意。不過,不論是否就範於商業化日記空間,日治時期的日記主人無可逃脫新時間單位的學習和使用。我過去已指出,「星期」這個新時間單位雖出現於清末臺灣,但逐漸被使用卻在日本治臺之後。受新式教育如黃旺成等人似乎很習慣於此種新時間單位,但是老一輩如林獻堂和張麗俊,在日記中卻也不約而同地會使用星期標記。林獻堂使用的星期單位的原因即是博文館的《當用日記》中即已印刷好每日的陽、陰曆日期和星期(曜日),自然不會混淆;但像張麗俊這樣未受新式教育的傳統文人,在他自己編印的十行紙日記中,卻中規中矩、自動自發地在日記中標示每天的星期(曜日),可以顯示新時間制度對一般民眾的滲透力。不過,張麗俊的日記中有標記星期的時段只到1919年為止,此後他不再擔任保正工作,或許因為與殖民政府沒有太多公務接觸,自此之後他的日記裹只有陰陽曆對照,星期單位自此消失,似乎顯示「星期」這種時間單位對張麗俊而言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
除了上述討論外,日記主人如何在這些有限的空間中取捨一天二十四時的生活內容?這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此處無法詳述,只能先提出一點簡短片段而極不成熟的想法。我以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得要將每一位日記主的日記全部看完,也就是要跟著日記主人過他的一生,從中掌握日記主書寫日記的目的、習性與特徵,才有可能理解日記主習慣偏向什麼類型的記事或關切什麼樣態的事物,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在不同時空處境下的習性和關切也會有所變化,因此要綜覽全局,才能掌握其中的變與常。如果能夠閱讀更多日記,便能觀察不同世代的人書寫日記的異與同,看到世代之間心態的轉變。4另一個面向則是針對同一重大事件對照不同世代日記主人的記述與反應,體會世代共同但卻又相異的經驗與記憶。
2014年11月20日起,高雄歷史博物館舉辦了為期半年的日記展,展場中有一面白底紅字的大牆吸引了我的目光,也可以呼應前一段文字所指涉的經驗和記憶。那是策展者將1945年8月15日當天,不同日記主對這一歷史性時刻的話語的堆疊。有人「嗚呼」有人「愴惶」;有人以為是「歷史大轉換」,有人卻認為將是「平靜的推移」;有人期待「光明的前途」,卻也有人感受到「一種的不安」。簡短的文字中鑲嵌著終戰之時,日記裹激動的、低吟的、喟嘆著、期待著,甚至難以言喻的話語,投射出每個人對盼望已久卻突然降臨的「非常道」,以及對即將消逝和即將來臨的複雜心緒。日記雖具有極高的個人特性,但也可反應同時代的某些共有記憶與心性。1945年8月15日,或許是揭露那個時代人們心智的中繼點,日記能否成為歷史的關鍵,就隱藏在這中繼站向前向後的延展之中。且讓我們由此翻開日記,往前追溯那激動話語的前生,往後翻閱低吟喃語的後世。
NOTE
Jorn Rusen, “What does ‘Making sense of history’ mean?”, in Jorn Rusen ed.,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N. Y.: Berghahn Books, 2006, p. 2.
吳玲青,〈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為例〉,《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8期,頁5-34。
參考吳玲青〈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附表:《臺灣日日新報》日記本販售記事。
這個主題,曾士榮老師已有一部精采的專書《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可以參考。
延伸閱讀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和休閒娛樂〉,收入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369-400。
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生活: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臺北:稻鄉出版社,2013)
許雪姬主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2008)
Jorn Rusen ed.,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N. Y.: Berghahn Books, 2006.